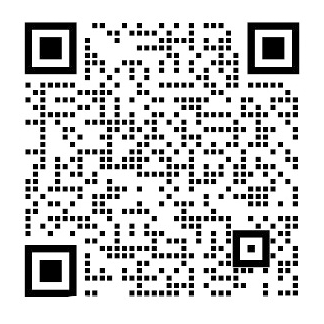-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1.幸福感
Ed Diener认为“幸福除了对情绪和情感进行评估外,还包括对生活满意度的认知判断”(Diener和Lucas,1999,第213页)。另一位学者Ruut Veenhoven(2008)的定义与此类似:“幸福是一种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对美好生活的认知以及一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感受到的愉悦情感。”总体而言,幸福感可被看作人类基于自身的满足感与安全感而主观产生的一系列欣喜与愉悦的情绪。尽管早期经济学家例如Smith和Marshall的一些研究展现了经济学对幸福感的关注,但在Pareto(1896)的“去心理化”效用理论及Hicks提出“消费选择理论”后,经济学家们就主要把目光投向可以“客观对应”的量度,如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等。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与其相关的研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大多数人包括经济学家认为是属于社会学或心理学研究的领域。直到1974年R.Easterlin提出“伊斯特林悖论”(Eeasterlin Paradox):在一国之内,富人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穷人;但如果从跨国比较看,贫困国家与富裕国家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从历时效应看,国家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国民平均幸福感的提升。自此,经济学界开始逐渐对“幸福问题”产生了研究兴趣。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幸福问题”正在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在人口调查中,关于主观幸福感和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的跨学科研究正在迅速发展。
目前最常用的测量幸福感的方法是调查问卷法,即通过研究对象填写问卷的方式来收集个体主观幸福感。虽然部分学者认为,人们在填写问卷时,可能会因为个人对幸福理解的标准不同,甚至个人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会受到周围其他人的反馈的影响,因此造成不同个体间的所做出的同一主观幸福感等级不可被同等相较。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偏差客观存在,这一类主观的数据仍可以大体有效反应人们的主观生活满意度。因此目前主流研究中仍采用调查问卷来获取研究对象的主观幸福感。(娄伶俐,2009)
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例如个体层面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健康状况等。这些因素并不一定和城市规模直接相关,但是城市建设的变化能够通过中介因素对城市居民内在心理因素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居民主观幸福水平发生变化。城市化虽然是经济发展的载体和产物,但本质内涵和最终目的应该指向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满意程度(幸福感)提高。因此,随着世界范围内“幸福研究”在经济学领域的复苏,有关于城市发展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的数量也逐年递增。
城市规模水平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
2. 城市化与幸福感
广义上,城市规模是指在城市地域空间内聚集的经济与物质要素在数量上的差异及层次性,主要包括城市的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和经济规模等。[2] 第一个用客观的方法来综合研究衡量城市和区域生活质量和福祉的是David Smith:他系统地研究了美国的社会福祉地理特征(Smith,1973)。这项研究基于不同地理级别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那时起,关于城市和区域生活质量(幸福感)的类似但越来越复杂的研究日益增长。
Arontt和Stiglitz(1979)在“亨利·乔治定理”的基础上,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城市地租与公共产品福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判断某一城市是否处在人口规模最优的状态。Mulligan和Carruthers(2011)指出,福利可以看作是“地区特定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私人还是公共的,这些商品和服务使得某些区域对于居民生活和工作特别有吸引力。“相反,缺少福利设施使得除此以外的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的吸引力”。在这方面的福利既包括自然环境(例如气候,自然美景,靠近山脉或海岸等),也包括社会或人为创造的环境(剧院,音乐厅,餐厅,公园,卫生和教育服务以及购物场所等)。Bartik和Smith(1987)以及Beeson (1991) 研究了按城市和地区划分的居民生活质量的特定客观指标,并确定了影响其质量的因素:自然环境和城市生活福利设施。特别是后者可通过相关公共政策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产生影响。Robinson,Murray-Rust,Rieser,Milicic和Rounsevell(2012)的研究采用了基于主体的建模方法来探索区域土地系统动态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联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们建立了基于主体的模型,并使用该模型来模拟诸如“绿地使用权”,公共交通和“购物便利”等指标对研究对象幸福感的影响。他们的结果表明,总居民的生活质量随发展密度的变化呈非线性增长,而产业发展的集聚对幸福感有积极影响。Mprrison(2011)使用新西兰12个地区的调查数据表明,生活在高度城市化的密集环境中会降低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衡量指标。Berry和Okulicz-Kozaryn(2011)则对美国城市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并发现小城镇得分较高,这可能是由于相较大型城市,小城市的自然环境和人均用地占有率更好,这些小城市风景更佳,空气清新且犯罪率低。Case和Shiller(2003)对所谓的“魅力城市”进行研究,认为这些城市的特点是娱乐业,高科技产业发达,以及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吸引国际名人定居。Gyourko,Mayer和Sinai(2006)的研究讨论了所谓的“超级明星城市”:与“魅力城市”相反,“超级明星城市”的房价成为主要影响因素,住房需求超过供应,并且供应受到限制。在这些城市中,财富驱动不同人群做出不同的选择:高收入人群会付更高额的房租,而低收入人群选择增加通勤的时间。Whisler,Waldorf,Mulligan和Plane(2008)的研究中为居民幸福感与公共品之间的影响关系增加了“生命历程”维度,突出寻找根据个人特征以及公共设施的类型和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整个人生过程组中,福利设施的价值各不相同。他们根据QoL(居民生活质量)指标考察了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在大城市中的迁移模式,他们的研究表明,文化和娱乐设施对于年轻人特别重要;与此同时,居住地的环境舒适与否以及安全问题对年纪较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更有吸引力。
国内有关幸福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有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化中居民幸福感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倪鹏飞等(2012)认为幸福感是一种长期稳定的指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同一指标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我国城市幸福感在空间上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特征。孙三百等(2014)认为我国城市规模与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在城市人口规模到达最低点前,人口涌入使人均居民消费公共品下降,从而呈现负向的规模效应,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逐渐降低;当到达最低点后,城市人口所带来的税收规模可以支持政府建设一些大型的、高质量的公共消费品,例如高层次的医疗教育机构、体育娱乐设施、大型火车站、地铁及国际机场等,呈现正向的规模效应,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拟合模型表明该曲线最低点处城市辖区人口规模约300万人左右。党云晓等(2018)基于环渤海地区44个城市调查问卷数据,通过多尺度建模分析,得出居民幸福感在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降低了我国“特大城市”的居民幸福感,积极的环境评价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良好的社会治安与人文环境对居民幸福感影响为正。余亮亮等(2019)通过对在城镇购买房屋的农民反馈的数据研究,证明拥有城镇商品住房的农民比没有拥有城镇商品住房的农民的幸福感更高,居住状况更好的农民幸福感更高。孙晓雪(2018)研究了通勤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通勤时间与居民个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东部地区人均通勤时间最长,居民跨区通勤需求较高,建设“中心城 卫星城”的城市交通体系势在必行;西部地区人口集中向省会流动,但西部地区交通建设较落后,通勤质量不断恶化,例如甘肃省兰州市道路拥堵情况不断加剧,导致居民幸福感不断下降。靳文博等(2018)从城乡规划的视角出发,研究了我国城市用地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均居住用地面积和人均道路用地面积与居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均绿地面积与居民主观幸福显著负相关。其中人均绿地面积与幸福感负相关,可能是由于主观幸福感受到住房和通勤的影响更大,而城市绿地挤压了居住和交通用地的面积,因而导致了两者之间的负向影响关系。
虽然城市规模、自然条件及各种福利设施对居民幸福感有何影响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关于城市各项建设用地指标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怎样的影响关系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把城市分解成各个建设用地指标并将其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关联,通过研究各项建设用地指标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而进一步为城市空间优化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以上是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