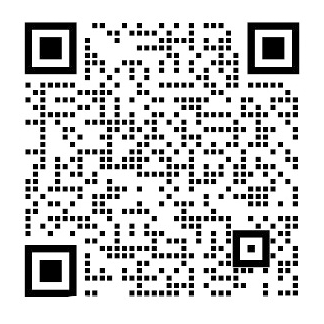文献综述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作者“退隐”文坛近十年后“归来”的力作,于2015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部系列作品是作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酝酿的,作者有意以三个不同时代为背景,写作三部曲,实质上表达了同一主题,这一主题,后来被集中概括为“乌托邦”、理想、幻灭等关键词。作者通过花家舍在三个时期的变化对照,以及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波折,探讨了百年中国社会中乌托邦的起落轮回,以及百年中国人的精神困境。面朝当下的时代,文学因为无法抗衡日趋物质化的社会生活秩序而渐渐躲在观望的阁楼,格非则试图逆时代而行,唤起人们心中渐行渐远的乌托邦精神。作家俯瞰历史变迁,试图探究人精神维度的理想乌托邦在历史中的嬗变过程,探寻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价值和存在价值,这种新的精神维度具有深刻的指导性意义。自《人面桃花》问世至收官之作《春尽江南》的完成,“江南三部曲”都备受关注,学术界也不断对其所作出的研究也,这些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针对“江南三部曲”的叙事视角、风格、结构和技巧进行探究。
一些作家认为“江南三部曲”是作者的创造由先锋回归传统,回归现实的转型之作。例如刘煜《传统叙事的承续与对接——浅谈格非“江南三部曲”对中国传统叙事的回归》,在此文中,刘煜认为“格非的创作在叙事上明显的体现出了向传统叙事靠拢的趋势,其系列作品lsquo;江南三部曲rsquo;,则更是在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上开启了其对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回归征程。”文从完整叙事与悲剧意识,全知视角与整体审视,情节中心与传奇演绎这三个角度来论证格非向传统叙事的靠拢。同样,杜慧欣《论“江南三部曲”中的传统叙事》也指出了小说里运用的三种传统叙事结构:“奇书式”结构、“传奇式”叙事和“寓言式”叙事。宋亚西《向传统文学的迁徙之路一论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首先从格非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入手,考察其在理论上对传统文学的审视和理解,在此基础之上,勾勒出格非文论思想发生迁移的路线,其后界定传统文学对于格非的意义。继而探讨格非精神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传统文学的新发现: 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和出世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格非本人以及格非笔下的知识分子身上均有体现。正是这种矛盾的冲突很好地解释了格非的文学创作心态及他笔下人物的精神特质。作者认为“江南三部曲”的现实主义倾向已经完全超越了格非早期所钟爱的现代主义,格非是带着一种和缓的先锋性走向中国古典传统文学。正所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格非既没有抛弃西方理论对他的影响,也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学的过程中使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学得以继承。臧浩然《论格非lt;江南三部曲gt;对先锋小说的延续与发展》中指出,“江南三部曲”与以往先锋小说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它向“小说”的回归。格非在叙事中设置的起源性的空缺或故事的历史性构成中的关键部位的缺乏这些先锋时期的技巧仍有体现,但是并没有造成故事情节的断裂,空缺不再是无迹可寻的形式游戏,而是成为了耐人寻味的悬念;其次,审美意蕴上,作品向中国古典小说借鉴资源,以唯美感伤、富有古典韵味的文字描述精致的江南生活;最后,思想主旨层面上,“三部曲”横跨中国自清末到当下的百年历史,以“新历史”的写法传达作者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世道人心的独特思考。总而言之,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江南三部曲”是一次先锋和传统的结合,是现实的回归与先锋的延续。先锋精神的价值是对内心体验和存在状态的真实表达,如果先锋没有革新,一味重复,将会丧失其内在的生命力,也是有违先锋精神的初衷。“江南三部曲”则是作者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将先锋与传统,乃至古典结合,赋予了文本更多意义。
另一些作家通过此作探讨了格非的诗性写作。王侃教授在“江南三部曲”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将格非称为“诗人小说家”,认为在格非以往的小说中有一种“特定的诗性”,“诗人小说家需要一个诗性的诱因驱使他写小说,这个诱因应该是从历史或者时间当中剥离出来的一个情境或者某一个印象,这个从历史从时间当中剥离出来的东西,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纯粹美学的东西。”而在“江南三部曲”中作者多次通过寻找内在的逻辑的方式把有巨大差异的两类人、两个画面连缀在一起,构成了一种“诗性”。而格非在《人面桃花》中讨论的“革命”超越了革命本身,他想讨论的“不是革命,不是历史,而是感时伤生”,是萨特所说的“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而这正是诗人小说家的意味,是三部曲最重要的修辞。张学昕《lt;人面桃花gt;的诗学》里也指出,格非似乎要 表达、 重现是记载、保存世间万事万物的转瞬即逝,用“人面”“桃花”这两个大的意象来控制千丝万缕的叙事线索,而且“让写作时的感觉与所描述的事物彼此寻找,召唤和通联”。新的时间感的建立也是这部小说进入诗学领域的重要因素:时间就是小说中的人物、事物存在的状态性,在叙述中时间被诗化,人生被诗化。格非已打破外在时间,创造出一种内在时间,在一种迷离、恍惚、模糊的诗性感受中把握存在和永恒。刘煜超《格非“江南三部曲”诗性写作研究》从诗性角度展开分析,试图通过小说语言、叙事、人物形象来探究格非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如何继承中国诗性传统,进行诗性写作,展现出对人的命运、存在及其意义的终极关怀。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其他文本对格非创作的影响方面来考察“江南三部曲”,例如赖奇志《论lt;红楼梦gt;对格非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以lt;人面桃花gt;lt;山河入梦gt;为例》,从叙事艺术、悲剧品质和禅宗思想三个方面阐释。周新民、朱旭《论“江南三部曲”与《红楼梦》—以“江南三部曲”超现实空间的建构为考察对象》着重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中“梦幻”这一超现实空间的建构对《红楼梦》的借鉴和发展变化。
二、从主题层面对“江南三部曲”中呈现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问题进行的批评探讨
这一类研究观点和相关论文较多,在研究中占据主体地位。代表性的作品有谢有顺《革命、乌托邦与个人史——格非人面桃花的一种解读方式》,李遇春《乌托邦叙事中的悖反与轮回——评格非的lt;人面桃花gt;lt;山河入梦gt;lt;春尽江南gt;》,赵振杰《现代乌托邦寓言的悖反式书写——论格非“江南三部曲”的修辞指向》,王增宝《欲望与文明:乌托邦的命运——重读格非山河入梦》,敬文东《格非小词典或桃源变形记——“江南三部曲”阅读札记》等。谢有顺认为,《人面桃花》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广大的人心世界,从而为解答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和乌托邦实践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文学图景。格非在这些人的乌托邦实践中看到:任何一个梦想的形成,以及这个梦想之所以会走向它自己的反面,都是因为梦想的主体是人。是人,就无法规避他内心里与生俱来的欲望,也无法完全放下他心中的“执念”,这也就是任何一种乌托邦冲动付诸实践之后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李遇春指出,“江南三部曲”超越了乌托邦叙事与反乌托邦叙事二元对立的叙事陷阱,体现了作者将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视域融合的叙述诉求。他的论文从小说叙述结构去破译作者乌托邦叙事的策略和意图。在这三部曲中,格非不仅揭示了百年中国乌托邦进程中的历史悖论,而且暗示了这种历史悖论中无法摆脱的集体无意识力量,因为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在本质上都属于集体无意识范畴。格非在《人面桃花》中不仅写出了古典江湖乌托邦的破产,而且也写出了现代革命乌托邦的危机。格非在《山河入梦》中既写出了红色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冲动与灰色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冲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写出了红色乌托邦冲动内部的裂隙和矛盾,还写出了两种不同性质、不同色彩的乌托邦冲动之间的融合和交集。而《春尽江南》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经历了由现代性追求转向新保守主义的精神嬗变。赵振杰在《现代乌托邦寓言的悖反式书写——论格非“江南三部曲”的修辞指向》一文中提出问题并进行论证:格非为什么对悖反性叙事情有独钟?为何如此执迷于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与书写?面对正统宏大叙述的话语霸权,他如何开辟出一条有关百年中国知识人精神反应史的思想脉络?他从思想维度指出“江南三部曲”隐在的悖反性症候,并进一步揭示出执着探寻人类如何在贫乏年代里诗意栖息的知识分子所必然面临的精神困境,即“纠缠于乌托邦渴望和乌托邦恐惧的矛盾情感”之中的反抗。从叙事结构、修辞、语言各层面剖析格非长篇三部曲如何在融合中西方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资源和叙事技巧上实现对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悖反式书写,同时揭示其“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叙述”中所暴露出的思想概念化、人物符码化等创作缺陷。从文本特征上,探悉“江南三部曲”中一以贯之的格非式的诗学特质,并通过撷取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意象来透视格非对生存、历史、欲望、幻想、传统、制度等一系列本源性命题的充满矛盾性的诗性哲思和艺术勘探。
龙慧萍《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研究寓言研究》与姚建斌《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存在的艺术》等在总体上探究乌托邦小说的论文中也用较大篇幅去解析“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建构。
以上是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