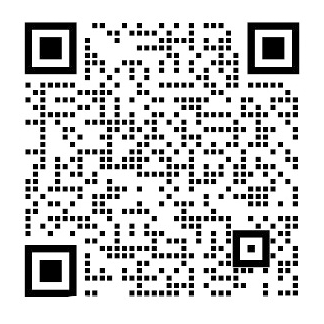文献综述
阿来是我国著名的藏族作家,是《尘埃落定》的作者,并于2000年凭借这部作品获得当年的茅盾文学奖。阿来的藏族血统来自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则是一个把生意做到川西北藏区的汉族人,阿来出生和自小生活的环境即是大渡河上游的“嘉绒藏族”村庄,属于川藏高原的一部分,这里的藏族世世代代过着半牧半农耕的自然生活,这给阿来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阿来的许多作品中。在《尘埃落定》中,阿来更是把这点融入时代,将土司文化的特点与变迁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民族和文化的交融、冲突中体现出来。
自《尘埃落定》获奖以来,学术界对其关于民间文化、表现手法、审美特征、哲学意义等多方面进行了很多研究,有人从民族学角度予以探究,认为小说中的神秘主义叙事更多得来自于藏族苯教文化,本土民族文化资源是作品神秘主义叙事的根基。有人站在文学本体论的立场进行探究,认为《尘埃落定》在题材、叙述视角、语言三大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陌生化”现象。有人站在比较文学的的高度,仔细对比《尘埃落定》和《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等世界名著之间的异同。然而在对于文化冲突的体现方面,研究成果还比较少,目前学者对于《尘埃落定》中的文化研究主要有几种类型:一是从宗教文化入手,解读苯教文化对土司制度的特殊作用,探寻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走向,借宗教文化来解读小说,分析小说中民族化叙事的前因后果;二是引入其他文化要素和观念,对小说中表现的藏民族文化进行分析和解读,如民间文化、女性文化等等;三是从文化变迁的角度对《尘埃落定》中土司制度解体和土司文化的衰落进行分析。以上三种研究方向和笔者关注的文化冲突要点有一致的地方,如研究文化冲突的前提是必须先全面完整地理解书中体现的种种文化,尤其是涉及根本的民族价值、文化观念以及政治经济观念,研究文化的变迁也要了解文化变迁的动力和方向,这就涉及到小说中土司文化自身内部的演变和外部文化对土司文化的冲击这两种文化变迁的动因,在此,笔者选取的是文化冲突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契合了小说的背景——风云激荡的上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经受着外部冲击,而四川阿坝地区的土司制度是这一时期全中国的缩影,不断地遭受着外部的冲击,其中有汉民族文化的冲击,也有外来的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冲击,而这些文化冲突正是阿来着力表现的,他用民族化的叙事和傻子少爷的视角将民族间的冲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显性的冲突,如军事政治经济冲突,是宏观;另一种是隐性的冲突,即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是微观。两种冲突相辅相成,并将民族间文化的冲突集中在傻子少爷的观念和言行中,从叙事层面把握住了民族冲突的显性和隐性、宏大背景和微缩细节之间的关系。
所以,要研究文化冲突,就必须结合多个角度,并且从外部文化冲突的动因出发,来研究土司文化的变迁,还要结合政治经济社会要素,从宏观的角度对文化冲突在书中的表现和作用进行铺垫和阐述。为此,笔者在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共参考了14篇与该选题有关的文献资料,其中7篇是关于《尘埃落定》的历史文化观以及文化变迁的论文,2篇是关于书中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论文,5篇是关于《尘埃落定》的民族化叙事结构的论文。要分析小说的深层文化内涵,就必须从这些小说的表层进行分析,如小说主题、叙事手法、结构安排、人物形象等,由阿来的民族文化背景和小说的主题决定了这些的表层特征都凝结着深层文化内涵的结晶,是和小说主要表现的文化冲突相联系并相辅相成的。
首先,为了对《尘埃落定》中的文化冲突有全面的了解,我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尘埃落定》与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相联系,用这两种文学批评方法对小说进行分析阐释和总体把握,可以发现整部小说的总体文化主题是“变迁”。由小说中的诸多文化要素的演变和新要素的加入,最后汇聚在典型人物——傻子少爷的视野下,由他的言语行为对这些小说中出现的要素进行社会角度的“评判”,做出选择,并和典型环境中其他人的言行形成对比和反差,在塑造傻子少爷人物典型形象的同时,揭示了土司制度变迁、瓦解的原因。
其次,在叙事手法和结构安排上,阿来使用了鲜明的民族化叙事手法。不同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切入角度,也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秦敬在《论lt;尘埃落定gt;的复调小说特征》中认为阿来在对小说故事的叙述中采取了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复调手法,对人物自我意识的艺术描写以民族文化和文化冲突为准线,使叙事的组织和情节的安排上有法可循,让小说中的人物循着这条准线推进故事,而作者本人则退居文本之后,结构布局上的惊险情节及众多脱冕型结构的运用更使小说呈现出强烈的狂欢化文学的特征。这一特征正是作者藏汉混血的艺术思维及对嘉绒藏区独特历史文化形貌的考察相结合而产生的 ,也是作者借“傻子”这一艺术形象传达个体生命浮沉及社会历史变革的重要手段。毛莉菁在《论lt;尘埃落定gt;的叙述方式和叙事策略》则更多地从人物角度把握小说的叙事结构,她认为《尘埃落定》刻画了“傻”与“不傻”相结合的独特的人物形象,同时作家又通过“小我”与“大我”相结合的小说人物和叙述者相分离的叙述方式和叙事策略,既符合人物特质的展示,又显示了自身的审美意义,显示了作家新的小说观念和新的艺术探求。郝敏则在《论lt;尘埃落定gt;叙述视角的审美意义》中从现代主义文学的真实感和荒诞感的矛盾角度出发,对傻子少爷的人物形象及由此引发的和周围环境人物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解释,从文学技巧的角度分析了小说叙述手法和结构安排的审美意义。
最后,要理解《尘埃落定》及其中的种种冲突,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傻子形象在小说中的重要作用,阿来设置了这个人物形象的目的是多重的。第一,傻子形象构成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的特点之一就独特性,在典型的藏族土司家族之中诞生一个言行怪异的傻子,并且是汉藏混血,傻子少爷的形象和血脉在书中是一个标志、一个符号,标志着土司制度在外部冲击和内部演变的相互作用下开始土崩瓦解,到最后“尘埃落定”。第二,从叙述手法和人物形象的关系角度看,小说以“我”的第一人称视角叙述,是小说中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而“我”则是一个诞生在土司家族的傻子少爷,这就给小说带来一种叙述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感”,结合藏族土司文化和外部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具有民族风情和时代感的“陌生化”叙述效果。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讲,傻子叙述是一种限知角度叙述,里蒙bull;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中将这种叙述称之为“白痴叙述。第三,傻子形象和周围环境形成对比,他的言行看似无凭无据且和周围人物的行为大相径庭,但事实上有章可循,即所谓“天行有常”,具体到作品中,就是傻子形象和周围环境的联系和冲突,这种联系与冲突是土司文化内部冲突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缩影。学者们也对傻子形象进行了很多分析研究,梁洪润在《浅析lt;尘埃落定gt;中傻子的人物形象》中认为,傻子少爷“我”是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却又始终是一个旁观者、局外人。傻子并非没有头脑,而是逻辑与周围的人不一致,他每天醒来问自己的“我是谁”、“我在哪”的问题,充满着哲学上“终极追问”的意味,梁洪润认为傻子的傻是自下而上的智慧,是人性丰富的形态,使他能够较其他“聪明人”更完整地见证并预言自己部族的命运。更多的学者形容傻子为“大智若愚”,认为阿来将土司制度内外部的矛盾冲突和谐地统一在他身上,体现了傻子的政治经济智慧,但在这种智慧背后,隐藏着的是一条文化的主线,是傻子所接受的文化促使傻子形象的一步步发展,相比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超前性使傻子能够预见未来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在这种发展和预见中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见证了土司制度的瓦解。而这条文化主线又建立在特殊的民族时代背景上,所以说傻子形象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息息相关,相辅相成。
由于目前对于《尘埃落定》中的文化冲突的研究并不多,因此笔者在选择阅读参考文献时,范围有所扩大。我们除了对涉及文化相关内容的资料进行参考,也对研究《尘埃落定》富有特色的叙事艺术、结构安排和人物形象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收集,以期能够在分析研究透彻小说文本特点的前提下,用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方法,将小说的这些特点与民族间文化的冲突相联系,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发掘小说中文化冲突的表现和作用。结合小说所叙述故事的时代背景,我们还搜集了关于小说历史观的文献资料,着眼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发展放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民族背景中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完整而无偏颇地解读小说中的文化内涵,这也是正确理解小说文本的前提。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多数研究者都专注于对《尘埃落定》中某一文学特点或从文化的单一角度对小说进行解读,而对于这些特点在文本中的体现与文化之间的结合有待进一步探索。由文化冲突分析《尘埃落定》,将小说中的突出特点与文化背景相结合,为分析《尘埃落定》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利于对作品整体有更全面立体的把握,所以这个角度的引入将为当前对《尘埃落定》的文化与文学研究提供有意义的补充。
以上是毕业论文文献综述,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外文翻译、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